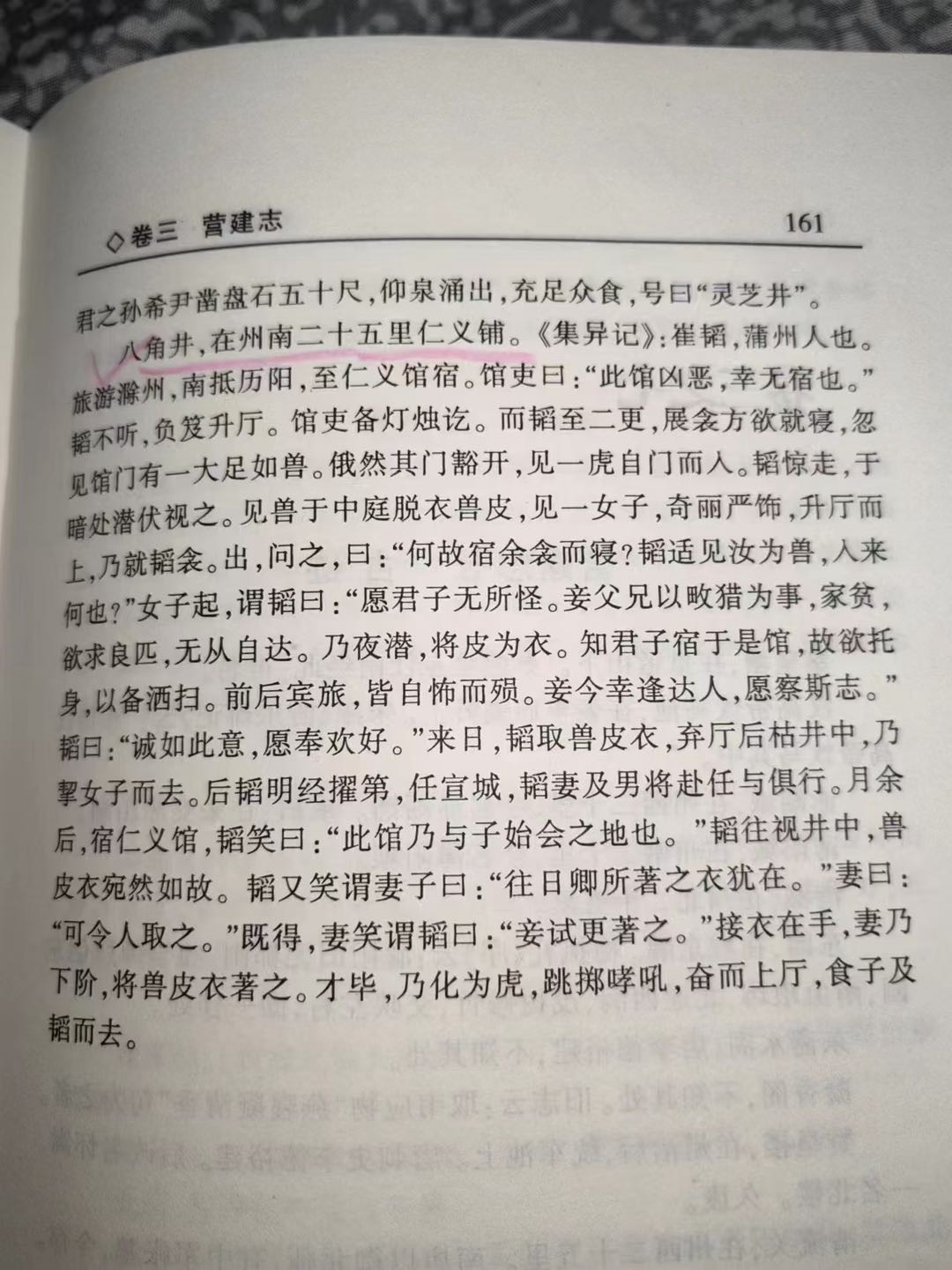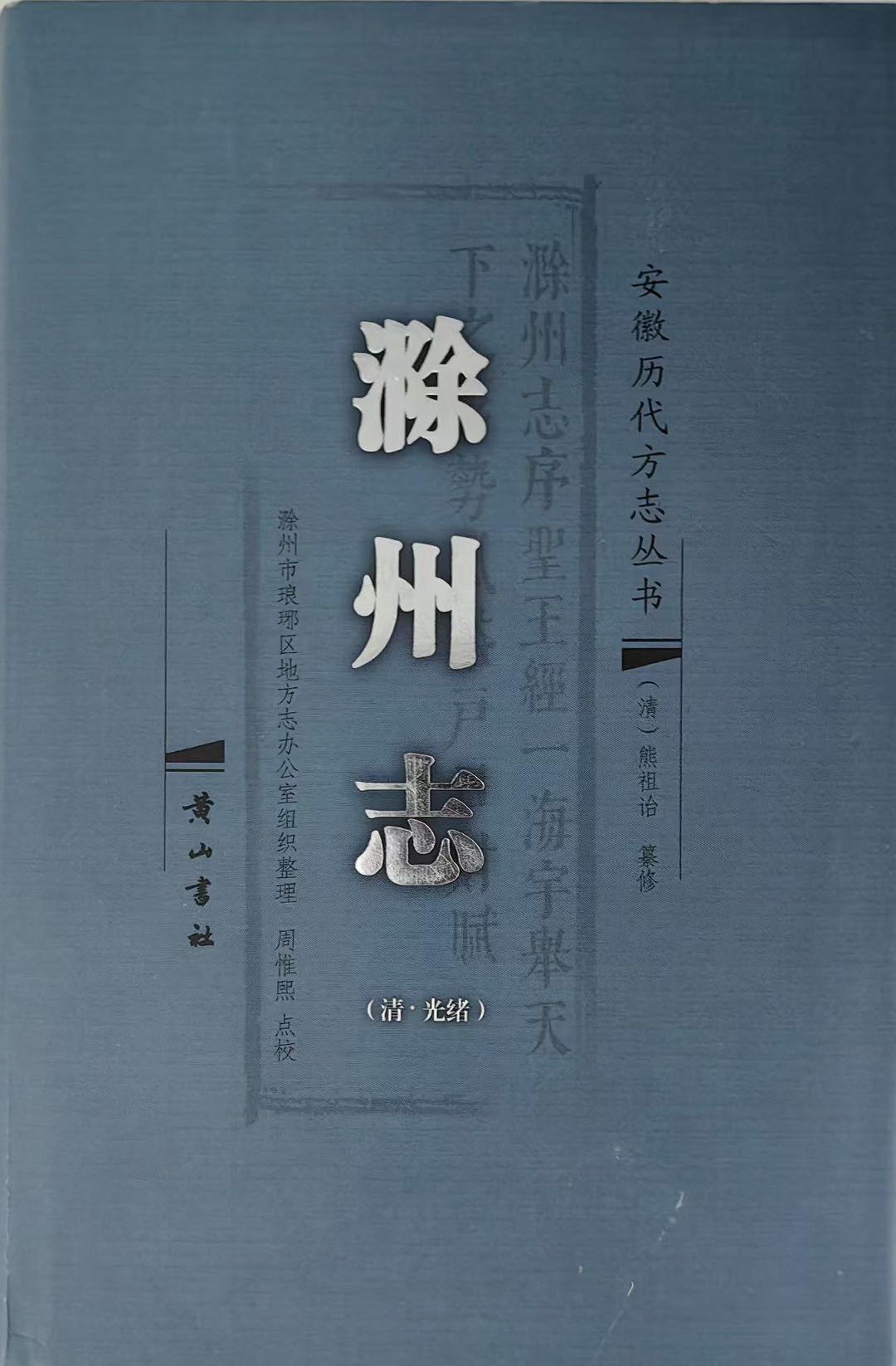《滁州志》卷三 营建志 161页记载滁州八角井衍生出这么一段故事:
八角井,在州南二十五里仁义铺。
《集异记》: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衣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女人君子无所怪。妾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
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后,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掷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
这段文言大致意思是:《集异记》记载蒲州人崔韬去历阳(今和县)经过滁州,晚上打算在仁义馆(位于滁州南二十五里仁义铺,即今天腰铺镇)住宿,驿馆官吏告诉他,这个驿馆不能过夜,夜里会有老虎来伤人。书生不相信,就坚持在馆里住下了。结果到了晚上,果然有老虎闯了进来。吓得他赶紧躲了起来并在暗中观察,然而这只老虎进入驿馆后,竟然脱下虎皮变成了一个美女,紧接着就是聊斋的套路……
后来这位美女陪着崔韬进京赶考,剧情需要也必然是金榜题名,美女帮他生了一个儿子,崔韬挈妇将雏前往宣城上任,再次经过仁义馆,二人便想重温旧梦,进馆以后,崔韬看见当初妻子脱下的虎皮还在八角井里,于是让人把那张虎皮捡起来,重新披在了妻子身上。披上虎皮后的妻子又变成了一只老虎,奔腾咆哮,把崔韬和孩子吃掉后逃之夭夭。
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如果出现在小说或者神话故事中也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但它出现在地方志里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人民大学毛立平教授是清史专家,当年读博士的时候,她的导师带着她去看材料,无意中看到了某地方志记载了以上情节,不知道她看到的是否是《滁州志》,抑或别的地方志也有类似情节。
毛立平教授当年是想做一些研究性别或者是女性的东西,她的导师看到这则故事后说:这个材料对你很有用。她觉得:这明显是神话故事嘛,能有用吗?导师说:你看这个是什么书籍?是地方志。地方志不是官府编写的,是地方的一些文人士大夫来编写的。他们为什么长篇累牍地把一个神话故事写在里面?这是有寓意的。如果跟一个不经过三媒六证、身份不明、就直接野合的女子在一起,婚姻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说明:地方志旨在系统整理地理、历史与文化,以存史资政、教化乡邦。